信息來源:2011年03月15日 科技日報
兩會爭鳴
“現在沒幾個年輕人愿意老老實實地搞科研了。”一見到記者,全國政協委員、河北工業大學微電子技術與材料研究所所長劉玉嶺就忍不住發起牢騷。他主持了一個3000萬元科研經費的國家科技專項,本想讓自己的幾個研究生畢業后回實驗室工作,誰知沒有一個人愿意留下來。一問原因,學生的答案是:“搞科研就要做冷板凳,怕自己坐不住,也掙不了多少錢。”學生最后的去向不是考公務員,就是去事業單位或國企。
“感覺在他們心目中,現在耐心搞科研沒有前途。”劉玉嶺認為,這肯定受整個科研大環境影響,原因在于當前我國科研人員價值觀出現了一定的偏差。
記者在兩會采訪期間發現,有過類似遭遇的不止劉玉嶺一人。
科研理想的現實困境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王志新從開始從事科研工作的第一天,就已經立志把此當做終生追求。“可現實狀況是怎樣的呢?看看現在我們每天都在忙啥就知道了:發論文、跑項目、報獎項、評職稱……不忙這些?我想,但做不到。”說起當前科研人員的現實困境,王志新嘆了一口氣,“就說跑項目吧。我們科研人員是真正的弱勢群體,手頭沒什么科研資源,與項目立項、評審、撥款等相關資源和權力都掌握在管理部門。不跑,就可能面臨沒研究工作可做;跑了吧,審批手續多,寫申請材料、課題驗收都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最后留給專業研究的時間是少之又少,我現在每天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研究專業問題。不跑行嗎?”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原總地質師茹克委員對此深有體會。在他看來,大多數科研人員熱愛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科學理想和追求。“現在科研人員的科研時間越來越少,但科技評獎是越來越多。評價有一定的激勵作用,但現在太多太濫,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扭曲了部分人的科研追求。”
“現在大多數科技獎勵都變味了。”他認為,調級別、漲工資、評先進等關乎科研人員切身利益都和科技獎勵的等級、數量掛鉤。導致部分科研人員急功近利,把跑項目、搞鑒定、報獎勵當成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慢慢嘗到甜頭后,反而沒有心思靜下心來踏實地做研究工作,時間一長,無形中助長了科技工作者心浮氣躁、弄虛作假的不良風氣,最后離真正的科研工作越來越遠。
“學術造假”背后的價值取向
“老老實實做科研出不了成果,投機取巧反而獲得了大量所謂的成果。”這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趙忠賢委員眼中科技界的“怪現象”之一。在他看來,在當前不良科研學風的影響下,相比于坐冷板凳搞科研的舊觀念,現在論文剽竊、抄襲等學術造假行為已成為某些科研人員獲取科研成果乃至其他利益的“學術捷徑”。
趙忠賢告訴記者,甚至有個別科研人員為了一己私利,不惜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與其說他們是在進行學術研究,不如說是為了實現某種經濟目的。“這就是為什么在我國有如此多的所謂居世界領先地位的科研發明、醫藥技術問世,卻沒有一次在本土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
對此,鄔賀銓委員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轉型期,誠信建設還剛剛起步,造假成本遠遠小于做假所帶來的豐厚的收益。當誠信得不到獎勵,而虛假得不到懲罰時,造假自然就會形成風氣,這股風氣也影響了科技界,具體而言就是踏實搞科研的人少了,通過學術造假等“捷徑”短期內獲取成果的現象時有發生。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第203研究所副總工程師徐中信委員對此深感認同,同時他認為這種扭曲的科研價值取向背后的利益驅動因素不容忽視。他以李連生撤獎事件為例:“校方不揭發李連生造假行為,無非是為了維護學校的一己之利:可以憑借獲獎爭取更多的項目經費,擴大學校的知名度等等。歸根結底,這都是背后利益驅動的結果。”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鄔賀銓認為,當普通科研人員的“理想抱負”與“現實遭遇”碰撞時,他們就面臨著自己內心對科研價值觀的選擇:是腳踏實地求真探索還是隨波逐流?
“現在部分科研人員價值觀出現了偏差,出現了一些學術不端行為,不能把原因籠統歸結于各種各樣的外部環境。我認為科學家自身的價值選擇和自我約束非常重要。”鄔賀銓認為,“除了要出臺相關遏制各種學術投機、腐敗行為之外,當前最為重要的是要加強科研人員的科學道德教育,培養學術誠信意識,使科技工作者在面對各種誘惑和利益的時候,能做到自律。”
對此,中國科協副主席齊讓委員有著相同的看法。“針對學術腐敗,從嚴處置,提高不端行為的成本,也并非治本之策,我認為誠信和自律是最好的辦法。在這方面,科學共同體更要發揮教育引導的作用,幫助科研人員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樹立嚴謹治學態度和科學精神。”據他介紹,中國科協在2007年1月16日通過《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2008年11月發布了一份面向全國科技工作者的公開倡議書,目的即是要呼吁科研人員做到自律,旗幟鮮明地抵制敗壞學術風氣行為,堅守自己內心那份對科研事業的熱愛和追求。(本報北京3月14日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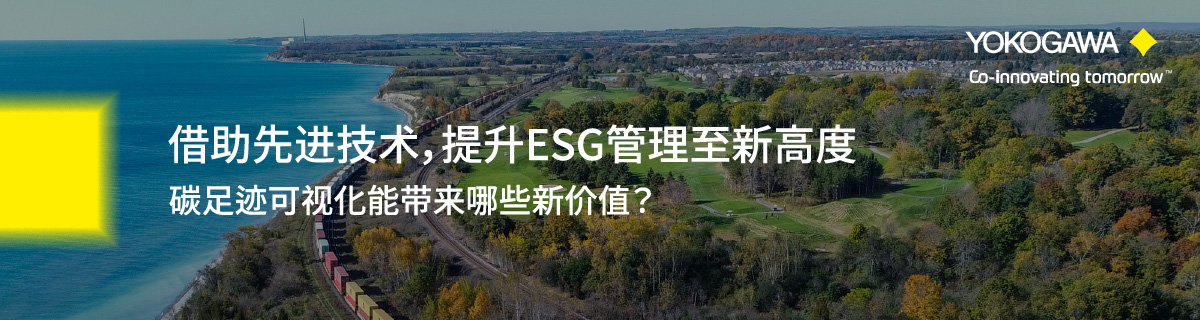




 資訊頻道
資訊頻道